余中先:摆渡,在文学之海
对于喜爱法国文学作品的多数中国读者而言,余中先一定不是个陌生的名字。他像是一条隐秘而坚韧的航道——四十多年来,他把百余部法语作品通过翻译“摆渡”到汉语世界,也把自己活成了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一张“活地图”。
而这条航道的起点,正是他书房里一张背窗而放的书桌。如今已经退休的他,每天依然雷打不动准时落座工作,开卷译事。阳光从他背后漫过肩膀,悄悄地给右手墙边那一排排摆放得满满当当的书墙镀上一层柔和的金光。书柜里,有这些年来余教授自己翻译过的书,有词典这类工具书,还有别人送来的珍贵外国老版书。书墙一直延伸到客厅的走廊上,像一条不肯靠岸的船,随时准备把下一部未被发现的法语作品泅渡到汉语的彼岸。
日前,由余中先所著的《从荒诞到反抗:导读加缪〈局外人〉和〈鼠疫〉》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报记者借此机会与余中先教授进行了一场独家专访,听他在这张书桌前分享自己如何以译笔为舟,载着冷门经典“逆流”而上的往事;又如何看待静水深流的文学之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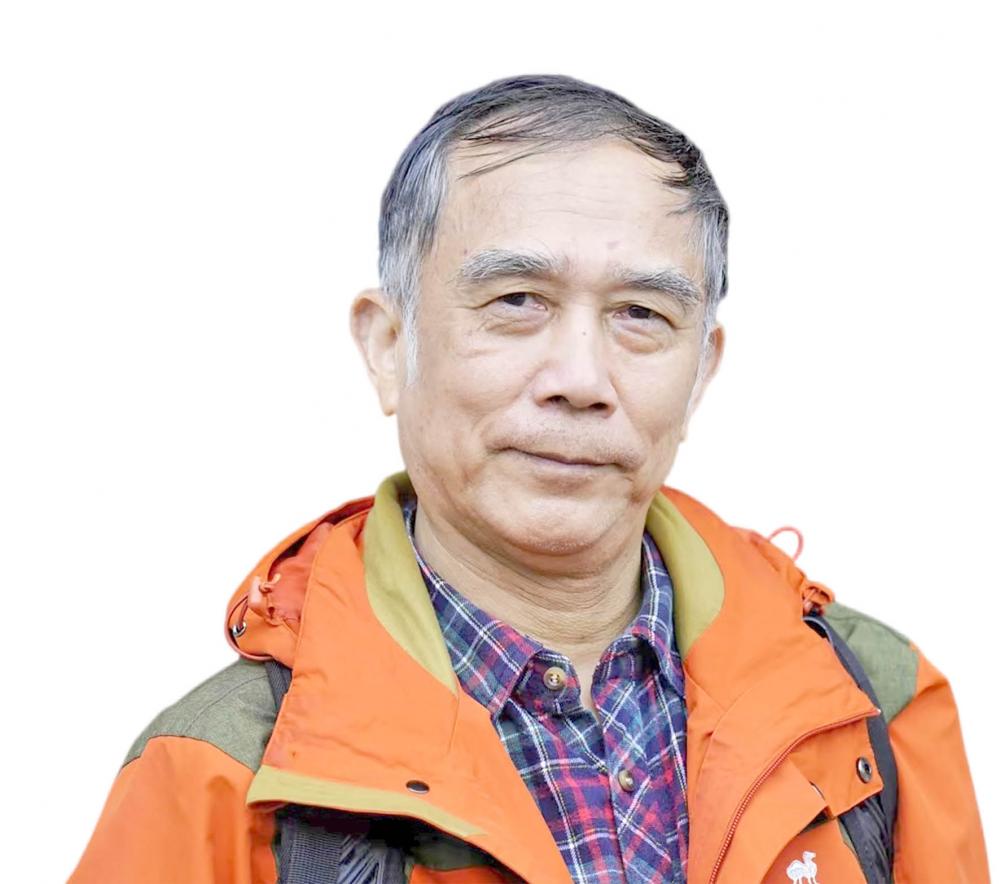
余中先。资料图
推开文学相遇之窗
回顾余中先教授过往的翻译史,不难发现他曾经着手翻译的众多法语文学经典作品,也是不少中国读者与遥远的法国作家们“初识”的契机。
1985年,余中先从北京大学法语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杂志社,从事外国文学的编辑工作。那时,《世界文学》几乎是中国读者眺望世界文学的“第一扇窗”。而余中先凭借对文学的热爱与法语专业积累,除了完成编辑的职责之余,也尝试翻译更多的法国文学作品。他在选择翻译文本时,尤其擅长发掘法国文学作品中的“冷门宝藏”,有着超越时代的文学洞察力和精准判断力。
1988年,余中先第一本正式发表的译作——弗朗索瓦丝·萨冈的《你好,忧愁》问世。这本写尽青春期迷惘的小说,初时发表反响平平,直到2006年重版后却得到了众多中国读者的喜爱。在他看来,这是因为聚焦两代人代沟的问题在中国出现得比法国晚,所以相关的文学作品被读者接受也就来得较晚一些。后来,他又把法国诗人、剧作家、外交官克洛岱尔也带进了中文世界,让汉语读者第一次读到“堪与莎士比亚的剧作媲美”的《缎子鞋》里的东方意象。2001年起,余中先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工作,选出的作家如让-马利·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安妮·埃尔诺等在后来获颁诺贝尔文学奖。
于是,一扇又一扇窗被悄悄推开——隔着时差与语种,让“遥远”的他国文学从此有了体温,也让“初见”成为了更多读者爱不释卷的“久别重逢”。
译者的“三重门”
从事法国文学翻译四十多年,又译介过上百部小说、戏剧和诗歌作品,对余中先而言许多作品的翻译过程都有着曲折奇趣的小故事。在这之中,“折腾得最厉害的”并最终成果能让他感到满意的作品,要数19世纪法国小说家于斯曼所写的小说《逆流》了。
这本小说讲述了作为贵族后代的主人公德塞森特,他厌倦了早年在巴黎的放荡生活,便幽居到郊区乡下买了一所宅子,过着一种被当时和后来的人认为是“颓废主义”的生活。这本书里虽然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但是作者努力用各种文字表达来描述主人公的丰富联想:德塞森特为每一种利口酒的滋味都类比一种乐器的音色,像是苦味柑香酒相当于单簧管,薄荷酒和茴香酒则像长笛;还对自己豢养的一只乌龟精心装扮,为其背甲镀上华丽的金壳,又在背甲上装饰珍贵的宝石。这本书以极尽感官之能事、辞藻华丽到近乎奢靡的“颓废美学”,将没落贵族世界的颓唐与精致一并封存于纸页。
而余中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关注到这本小说。法国《读书》杂志的专家团队早年曾在难以计数的图书中精心分类遴选出一批个人理想藏书的书目并做成读书专题,最后这些专题被集纳整理为一本名为《理想藏书》的图书,以便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提供一份全球经典阅读指南。当年余中先首次把《理想藏书》翻译过来后,就有人对照所选的法国文学篇目,发现有那么几本书尚未有中译本。其中,就有于斯曼的《逆流》。
余中先带着疑问去查阅了这本书,恍然发现这本小说要翻译过来确实存在较大的难度:书中不仅涉及到自然现象、社会生活、艺术现象、私人生活等各个领域的话题,还用了大量精巧华美的语言描写了当时走向没落的贵族社会历史风俗和享乐生活,可谓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百科全书”。也因为如此,这对译者的知识背景和文字语言水平的要求也相当高,让不少译者望而却步。于是,他索性撸起袖子自己上:2008年动笔,2010年交初稿,边查资料边做注,给这座迷宫配上了钥匙。
在他交付初稿的同一年,另一出版社刚好抢先推出了这本小说的国内首次中译本,书名译作《逆天》。但经过仔细验证并结合文本分析后,余中先认为《逆天》的译法更像是为了靠近年轻读者阅读习惯而选择的用词,“这种时尚的用法并不适合该历史时期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态度”。他认为,主人公隐居时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自己与自己较劲”,属于一种“逆行倒施”,但还未至于大逆不道的“逆天”,因此他坚持将书名翻译成《逆流》。后来他继续寻找并参考了多个版本的资料,不断优化译本初稿,还趁着访问法国的机会游历了与于斯曼有关的几处景点,才最终磨出了《逆流》的中译本。
在余中先看来,对于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三重门人们已经有过许多的讨论,而这三个字中如果能把“信、达”做到位,也已经是一份合格的翻译;至于雅与不雅,则要视乎文本的需求而定。他说,译者的任务就是:“理解,努力地理解,努力地让读者跟着你来理解。”此处的“理解”本身已经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比如,故事来龙去脉是否清晰、细节是否清楚无遗漏、人物性格是否遵从作者意图、时代特征有否交代、文字特色有否呈现等。
余中先表示,翻译是要让读者更多地去接近原作,不能单纯考虑译本是否易读,“译者是要带领读者去努力适应原作的内容和形式。”他尤其强调,译者不能因为原文的文字粗糙,在翻译时就自作主张把中文改“雅”,“这会让读者在译本里‘只见译者而不见作者’”。
文科并非无用
谈起自己写的新书,余中先说自己与加缪的缘分早在大学时代就已结下,他毕业论文研究的正是加缪的《鼠疫》。四十年来,加缪笔下的人物和思想,始终是他反复咀嚼的精神养分。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在听过他的一次讲座后,敏锐地意识到:这位资深译者对经典的独特解读,或许能成为年轻读者啃下“名著硬骨头”的一把钥匙。双方一拍即合,余中先也欣然提笔,将半生研读加缪两本重要代表作的心得,合为一本“不带学术架子”的文学导游手册——这便是这本导读新书的由来。
翻开这本小书,最直观的感受是“轻”:书中文字简练清晰,没有繁重的术语理论,也抛开了冗长的理论。读者可以轻松地走进加缪的故事,甚至对书中那些格格不入的小人物多一份耐心的观察、理解和宽容。或许,这就是余中先最想递出的“钥匙”:不必先弄懂“存在主义”这些过分抽象的概念,也不必急着给人生下结论,只需跟随里厄大夫去看病、跟着默尔索走上法庭,先看见“人”本身。然后就会发现,曾经高高在上的名著阅读起来原来也可以如此轻盈,却又如此结实。
余中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文科最大的“用”正是其“看似无用”。他表示,文学作品能展示人间万千活法。面对荒诞、虚无、意义感缺失,加缪笔下的里厄医生驱除无用的疑虑,只管埋头救治病人——这些故事像一面镜子,照见人如何守住本分、寻找微光。理解世界的复杂与他人的孤独,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力量;哪怕只是一次短暂的共情、一次对陌生命运的凝视,“无用”之思也能抵达深邃的港湾。
在采访的最后,回想起自己在中法文学翻译之间的“摆渡”的五十年时光,余中先教授谦逊地笑着把这份坚守解释为:“我不会干别的,就会干这个。”五十年只做一件事,在余中先看来不过是“坐下来就成了习惯”。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他准时把自己放到那张背窗的书桌前,像把一枚硬币精准地投进同一个投币口,投进去的是法语的声母韵母,掉出来的是汉语的字字珠玑。他说,翻译就是“把法国的好东西拿过来给中国人”,而法国文学那股“标新立异又追求极致“的劲儿,恰好成了他继续磨这把刀的理由。
对余中先来说,五十年如一日的摆渡还在继续,对岸是仍在生长的法兰西文学,此岸是愈发辽阔的中文世界,摆渡的人在来回往返,“一任潮水来去,他自独驭兰舟”。


